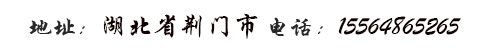古代文人的用香之道
|
中国香文化源远流长,从目前现有记载来看,香最早出现在上古时期,宋代丁谓《天香传》中记载:“香之为用从上古矣。”对香文化的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有3种因素,祛病、祭祀、文人雅事。 祭祀必不用多说,现代生活中一说到香,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寺院、庙堂等祭祀场所。上古时期除了用香祭祀以外,还会作辟邪除秽之用。 香在中医配药方面也有很大作用,其中苏合香就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香料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:“苏合,气香窜,能道诸窍脏腑,故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。”说的就是苏合香有调理五脏的功效,能祛腹中诸疾。 宋真宗就很推崇苏合香。 据《墨客挥犀》记载:“王文正太尉气羸多病,真宗面赐药酒一瓶,令空腹饮之,可以和气血,辟外邪。文正饮之,大觉安健,因对称谢,上曰‘此苏合香酒也’”。 宋真宗的这个酒之所以能让王文正身体康复,就是因为里面加了苏合香,可见此香的药用价值。 唐代以前,中原的香料并不多,唐代中后期才逐渐由西域诸国传入中原。范晔在为《和香方》所写的短序中说:“甘松、苏合、安息、郁金、(木奈)多、和罗之属,并被珍于外国,无取于中土”。其实除上述香料以外,可能还有很多其它的香料并不产于中国,因此,香料也是珍贵之物。 对于香文化的发展,古代文人雅士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,尤其宋朝时期,焚香、插花、挂画、点茶成为文人雅士之间的主流活动。古代文人除了品香之外,还会编撰香谱、制作合香、设计香具、制定香席仪规等,并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美学和哲学思想。 品香之法 说到品香,最快想到的便是“红袖添香”。古代文人在读书时旁边多会有妻子或是侍女为其添香,燃香的方式多为隔火熏香,具体是把烧好的炭埋一半在香炉的香灰里,把香灰压成小山形状,再在香灰上面放上云母片,将香粉或香丸放置在云母片上,借着下面炭火的热量,香气便会慢慢散发出来。如果是睡前读书,可添沉香,有助眠的功效,香气也比较淡雅;如果是晨时用香,可单添檀香或者以檀香、乳香、玄参合制的香方,有清热醒脑的作用。 除用炭香之外,还可以用线香,明朝初期以前的香称为“箸香”或“棒香”,因当时制香为纯手工搓制,故而做出来的香较粗,到了明朝后期才出现一个叫“唧筒”的工具,和现在的注射器差不多,用此工具才做出了较细的线香。 使用箸香或线香时应注意保持约1米的距离,即可观烟雾缭绕之美,又可闻到淡淡幽香。 香还可以与茶、琴、书画等项目相配,古代文人聚在一起品茶、品香、斗诗、作画,被引为雅事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有“独坐闲无事,烧香赋小诗”的咏香诗句。 合香制香 对合香的较早记载出现于东汉时期的《黄帝九鼎神丹经》:“结伴不过二三人耳,先斋七日,沐浴五香,置加精洁。”其中“五香”是指青木香、白芷、桃皮、柏叶、零陵香。古代文人追求情趣、意境,因此,在用香的时候也会想尽办法配制自己喜爱的香方,就连香器及焚香方法都有很多讲究。 琢瓷作鼎碧于水,削银为叶轻似纸; 不文不武火力匀,闭阁下帘风不起。 诗人自炷古龙涎,但今有香不见烟; 素馨欲开茉莉折,底处龙涎示旃檀。 平生饱食山林味,不柰此香殊妩媚; 呼儿急取蒸木犀,却作书生真富贵。 ——《烧香七言》杨万里 古代文人中制香高手颇多,如王维、李商隐、傅咸、傅元、黄庭坚、朱熹、苏东坡等。苏东坡曾在子由生日的时候,用檀香木制成的观音像和亲手合制的香篆做为礼物赠之“子由生日,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”。 斗香之雅 周嘉胄《香乘》卷十一有载,“韦武间为雅会,各携名香,比试优劣,曰香会”,说的是雅会斗香。这与斗诗、斗茶的形式差不多,都是古代文人雅士闲居里的娱乐项目或者是精神追求。 古代文人斗香极为讲究,从香品方面来说,香气的风格、香雾的形态、留香的时间等都极为考究苛责;从香具方面来说,香炉、香案的形态和材质以及周围的环境需要与香品的气质相投。 明朝文震亨《长物志》中有曰,在花园中焚香,最适合在天然形成的山石之上放置木鼎式的香炉,便更见山林野趣,有返璞归真之感。在香室中,则常布置一些用于观赏的名贵沉香,形如山峦起伏的沉香木,配以托盘托架,谓之沉香山子。 除此之外,文人雅士们还会将阴干香草制成的香囊系于衣袖中的肘臂上,香气自袖筒中隐隐散出,可谓袖底生香。唐冯贽《云仙杂记·大雅之文》中有记:“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,先以蔷薇露灌手,熏玉蕤香后发读,曰:‘大雅之文,正当如是。’” 楚国诗人屈原也有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”的诗句。其中所提到的江离、辟芷、秋兰都是香草的种类,除以配香囊以外,这几种香草也体现出了屈原的品性高洁。 由此可见,古代文人雅士对香的推崇已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,除了实际的用处外,更有尊敬与礼节的意味,正是因为他们的崇敬与热爱,“香”才能在后世发展成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度艺术品质的产物。 肆穸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suhexianga.com/shxxzjb/5252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云上植物课
- 下一篇文章: 药性指掌九十首,一文教你如何灵活运用中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