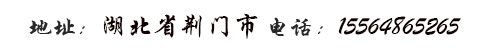香文化香气养性,熏香在汉代宫廷开始流行
|
中科白癜风医院爱心公益 https://4001582233.114.qq.com/ndetail_3913.html 明人画十八学士图 桌上承有汉代彩陶绘香熏炉 兴起于西汉的香虽属生活用香,却也并非仅仅被视为一种生活享受,其发展速度之快、地域之广,与“养性”学说在当时的流行有很大关系。汉初已很讲究养生、养性,“治身养性,节寝处,适饮食”。汉代儒学、中医、道家学说俱盛,无论是内圣外王的儒家、羽化登仙的道家还是应天延命的医家,都倡导“养性”,遵净心、养德、养性为养生之本。熏香既芬芳“养鼻”,又可清净意志、安和身心,且香气轻扬,上助心性修为,下增世俗享受,加之上古就有以香气享神的传统,因此,熏香在该时期得到推崇和流行也在情理之中。熏香,在汉代王族先流行 熏香在汉初的王族阶层已有所流行。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即发现了熏炉、竹熏笼(用于熏衣)、香枕、香囊等多种香具,内盛各种香药,如辛夷、高良姜、香茅、兰草、桂皮等。(墓主人辛追是长沙国丞相的妻子,其入葬时间约为公元前年,距西汉立国约四十年,比汉武帝即位早约二十年)从汉初的情况来看,战国(此时已有精制的熏炉)与秦代的用香应有了一定基础,西汉用香的跃进也是得益于前代的积累。西汉· 盛有香药的陶熏炉 到汉武帝时(公元前-前87年在位),熏香在各地王族阶层中已广泛流行,其既用于居室熏香、熏衣熏被,也用于宴饮、歌舞等娱乐场合。广州南越王墓(公元前年)曾出土多件熏炉,有的是乐师的随葬品,有的与铜钟、甬钟等乐器或壶、钫等酒器放在一处。迄今发掘的多个西汉中期(王)墓葬都可见熏炉、熏笼等香具及香药,也有十分精美的鎏(嵌)金银熏炉,包括带龙形装饰的高档皇家器物。西汉·鎏金银高柄竹节熏炉 汉武帝之后,皇室及各地王族的用香风气长盛不衰,所用香具也极为精美。汉成帝时有“五层金博山香炉”“九层博山香炉”。东汉末期,汉献帝宫中有“纯金香炉一枚”,“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,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,西园贵人铜香炉三十枚”。西汉·错金博山炉 汉代也常以使节名义遣商队沿丝绸之路西行,换取沿途的皮毛制品、香药等奢侈品。如东汉权臣窦宪(也是击溃匈奴的功臣)曾以八十万钱从西域采置了十余张毛毡,又令人用织物换取苏合香等物:“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,白素三百匹,欲以市月氐马、苏合香。”(《全后汉文·与弟超书》)用香,进入宫廷礼制 汉代用香的风气之盛还有一个突出的标志,即用香(熏香、佩香、含香等)进入了宫廷礼制。据《汉官仪》记载,尚书郎向皇帝奏事之前,有女侍史“执香炉烧熏”,奏事对答要“含鸡舌香”,使口气芬芳。《通典·职官》:“尚书郎口含鸡舌香,以其奏事答对,欲使气息芬芳也。”“鸡舌香”,形如钉子,又名丁子香,丁香,是用南洋岛屿“洋丁香”树的花蕾所制(非中国多见的“丁香”),其气息清香,常含在口中用以香口(似口香糖),但有辛辣感。东汉时的鸡舌香是名贵的“进口香药”。 含鸡舌香也成了著名的典故。人们常以“含香”指代在朝为官或为人效力,如白居易:“对秉鹅毛笔,俱含鸡舌香。”“口厌含香握厌兰,紫微青琐举头看。”王维:“何幸含香奉至尊,多惭未报主人恩。”魏晋后的礼制中关于熏香的内容渐增,其由来盖可溯及汉代。除了熏香、香囊、香枕、香口,汉廷的香药还有很多用途。汉初即有“椒房”,以花椒“和泥涂壁”,取椒之温暖、多子之义,用作皇后居室。这一传统长期延续下来,后世便常用“椒房”代指皇后或后妃。王族的丧葬中也常使用香药(借以消毒、防腐,先秦即有此传统),古代的文献已有所记载,如《从征记》载刘表棺椁用“四方珍香数十斛”,“苏合消疾之香,莫不毕备”,挖开其墓葬时,“表貌如生,香闻数十里”。《水经注》亦记之:“其尸俨然,颜色不异”,“墓中香气远闻,三四里中,经月不歇”。熏香在王族阶层的盛行对香的普及和发展大有推动之功,也开启了上层社会的用香风气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。目前的考古发掘表明,熏炉是汉代墓葬中的常见物品。据有关学者考察,岭南汉墓出现熏炉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,盖可说明当地的熏香风气更盛。岭南香药丰富,气候潮湿,又多蚊虫瘴疠之气,而熏香可以祛秽、烘干、消毒,这应是当地盛行熏香的一个重要原因。-END-撰文傅京亮图片 部分来源于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版权归“慧通香学研究院”所有,如需转载请于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suhexianga.com/shxgyzz/522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31天冲刺,新新老师划重点中药一
- 下一篇文章: 熏香避瘟疫,古人是这样做的